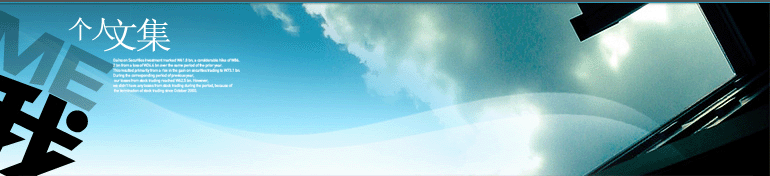|
梦梦的自白(1)
我姓孟,单名梦。据说出生之前我母亲做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梦,于是我便叫这么奇怪的名字了——孟梦。他们习惯叫我梦梦。
因为那个梦的惊吓,我母亲不喜欢我,当小我两岁的弟弟出生之后,父亲也忽略我了,毕竟那是他孟家的“唯一”血脉。也许是从小父母对我就不怎么关心吧,逃学打架基本男孩子做的事情我全都敢做,请家长是经常的事情,上初中之后我成了学校的混混头,父母实在受不了,把我送到了天津的姥姥家,让我在那里上学。不在他们身边又换了新地方,我不再打架斗殴出风头,原来那么做,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注意我还有这么一个女儿,现在没有必要了。我就在疼爱我的姥姥身边自由自在的成长。父母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,等我上高二时,那一年他们没有来,我不想回去,我知道回去也是多余的,他们还有弟弟。以后,他们每月寄来生活费给我和姥姥,算是不再来的补偿吧?我不知道。
高三上学期,姥姥过世了,他们都来了,仿佛陌生人般的面对着,我打算留在这里不再跟他们回家,他们没有说什么,留下一笔生活费,走了。其实我很想回去,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陌生的他们。之后我搬出去用他们的钱买了一间偏单——他们有的是钱,我要他们就给,以为这样就能弥补我失去的东西吧,好笑。再以后,我考上了大学,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户头,更省事了,有时要有大笔开销时,我打电话,他们就会汇钱给我。很讽刺吧,我象是一笔固定的金钱流出,对于他们。
梦梦的自白(2)
当别人开始上网时我也买了一台电脑,实在是无聊啊,远离了家庭又不住校。
网络是个好东西,它可以麻醉人让人逃离现实、陶醉于虚幻的快乐中,象是吸食鸦片。知道那是不应该经常碰的,偏又忍受不住它的诱惑,不可救药的沉迷其中,不想挣脱,就如此沉沦下去。
从大一开始,至今已三年,我唯一的网名便是“无色昙花”——梦是短暂的,昙花的生命仅有一现,苍白的梦境中,一朵失了颜色的昙花悄然开放、凋谢,却无人知晓。大一那年又一天我突然昏倒,去医院检查,是脑瘤。不知道是良性恶性,医生建议我全面检查定性治疗,我却只是笑笑,开了几付药离开——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忽视的感觉,这个社会的遗弃者,即使死了,也不会有任何人,流泪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,父母知道了也丝毫没有用处,如果注定我要死去,告诉他们只会徒增他们的伤心——如果他们会伤心的话。我想在渐渐的心的背离之后,我不和他们联系,他们会慢慢遗忘我的,原本人就是容易遗忘的动物。那么当我死去,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个消息,我是不可能“亲自”告诉他们了。
我不知晓自己还能活多久,过一天是一天吧,也许会一梦不醒,留在我营造的美妙世界里,腐烂、发臭,渐渐成了白骨才被人发现,到时候报纸的一个角落就会刊登出“某大学某女生死在家中xx天才被发现。……由此可见社会冷漠到了什么地步,我们应该……”而父母来认尸时回音我的腐烂气味吓得惊叫、面目扭曲……想到此处我就不禁冷笑,哈哈哈哈哈哈,真是好笑,他们会皱着眉与我凸起的眼睛相对,然后,一条蛆钻出来嘲笑他们,那时候他们会怎样啊,我狂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真好笑啊!我很他们。
我又晕倒了,这次是在课上——大三开学以来我上的第一节课。昏迷在最后一排,当我清醒时,天已擦黑,6点多了,有4个多小时我失去了知觉,教室里仅有几个上自习的,和我同班的那些人早就无影无踪。我的病加重了,昏迷的间隔越来越短。我起身离开,仿佛真的仅是做了一个梦。
就这么慢慢死去吧,我不再吃药,空虚的时候不是看书就是上网。龟缩在自己的小窝里,这真的是我的外壳啊,久得已然忘记太阳的模样,偶然出去,也是夜色一片。
(3)
我刻意逃离着人群,不愿与人交往,却无法阻止一些应该发生的事情——17岁以后开始有人追求我,不明白为何会看上我这种已经放弃自己的堕落者。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情的拒绝,不留余地。当我知道自己的病之后只能做得更彻底,不想欠别人也不想让任何人为我伤心。我并非无情却绝情,不仅仅因为我是没有明天的人,对任何人来说,我是累赘。
开始有人说我是毒药,爱上我的人毫无例外会中毒,在我无情的刺伤下,溃烂得体无完肤。
对于任何人,我仅是他们生命中的过客,他们仅是我的一场梦境,随便就能舍弃,遗忘。除了自己我已经谁也不相信了,没有朋友没有敌人。我是毒药,远离一切,靠近我只有伤害。
(4)
对于网络的虚幻,从头到尾我没有相信过谁见过谁,但我也不欺骗任何人,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否真实,我的真实别人也会怀疑,这都无所谓,谁认识谁呢。
那天一个陌生的名字陌生的人闯到我的oicq里——“毒药情人”。
“你为什么那么悲哀?”
我一愣,反问“怎么?”
“梦中的昙花梦中的自怜,寂寞包围着你,却是无色的梦无色的花,无尽的忧愁。醒来之后你还拥有什么?”
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的名字,可能的确是如此,我下意识的回避了很多,其实我仍是渴望爱与被爱。
“我说中了。”
“……也许。”
“你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么?”
“是吧……”
“那么你很漂亮了?”
“不”
“这样的自怜自艾,不是美女就是丑八怪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很冷漠,很自私,我看你是丑八怪了。”
“是的”
“这样说你都不生气?”
“嗯。”
“奇怪的女孩儿,我喜欢你的个性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想认识我么?我能够让你快乐,不再这么忧郁。”
“不想,再见”
我关了Q走了,被他开始的话吸引,却发现他原来和别人也没什么两样,无外乎是见面、上床之类。
“你好,奇怪的女孩,你不快乐吧?”他突然再次出现在陌生人栏里。
“什么叫快乐?”
“就是没有不快乐。”
“什么是不快乐?”
“你不开心、难过、迷茫、不知所措,鄙弃别人又被人鄙弃,你清高又希望能与别人交流,内心挣扎不堪……这就是不快乐”
我惊讶,没有想过他会说出这样的话,看他的资料:“真名:你去死生肖:空星座:空年龄:26毕业学校:打手中学工作:专业痞子自我介绍:我很帅我很坏,如果你是美女,就见面。千万不要爱上我,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——毒药情人”
“你快乐么?”
“我?快乐,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认识漂亮的女孩,寻找刺激,和哥们一起混。”
“这就是你的快乐?”
“当然,虽然庸俗,确是我得快乐。想必在你眼中我们这种人是社会垃圾。”
“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,却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的生活。”
“哦?”“……咱们见面吧!”
“再见”
“哎,怎么又再见?不想见就算了,不勉强你,接着聊聊。”
我沉默。
“走了吗?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……”
我哑然失笑,“你不是毒药么?怎么说我毒?”
“没走啊?嘿嘿,名字是哥们送的”
“哦?”
“因为至今没有女孩子能留得住我,我总是让他们心碎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害怕吗?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怕见到我就爱上我。”
“不可能”
“这么干脆,真不给面子。曾经有女孩子为我自杀。”
“死了么?”
“死了一个,另外两个活着。”
“厉害。你不觉的愧疚?”
“为什么要愧疚?又不是我让她自杀的,总不能为了别人勉强自己去接受吧?”
“……”
“虽然和我上过床,也不能意味着就代表什么,我没有强迫。”
“你……”
“不要说我不负责,这个社会有什么责任是我这种人能承担得起的?也许明天就在群欧中死去,说什么未来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招惹人家?”
“冤枉,是她喜欢我,我说过我的状况,她还是追我,当时她有一点反对,我就不会继续。”
“为什么要这样?”
“什么?”
“要这样做”
“……我是正常的男人,有寂寞迷茫混乱的时候,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,不知道生存的意义是什么,这样能让我快乐,证明我还活着。”
“……”也许他没有错,也许我们是一类的人——任性自私,为自己而活,却背经离道,世人无法认同。我把他加为好友。
“该走了,下次再聊,你才把我加为好友啊?够狠心~”
“知足吧,算上你不到十个。”“走吧你。”
“哦?那我该放礼炮庆祝一番了。”
“讽刺?”
“实话,走了,约ppmm了,88”
我看着他最后一句话,哭笑不得。
(5)
时间仍在继续,我的生活没有多少变化。课去的越来越少,学校向我警告,我当作不知道。开除又能如何,也许没等毕业我就死去,生命是自己的,不想不愿浪费在学习上。我主动退学。建立没有人反对,他们托人给我找工作,我拒绝了。于是钱照常寄来,不过多了些。于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很多地方。虽然没有什么周游全国的愿望,能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。
只有一次,我在海边晕过去,醒来的时候,一弯新月斜斜挂在天际,海水蔓延在我脚下,一侧身,一只小螃蟹横行爬过,沙滩冷冷的,只有海浪的低吟。我失声痛哭,没有原因。
很久,“怎么了?”我抬头,关切的眼神、慈祥的面容,一对相携散步的老夫妇关切的望着我,老奶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给我披上,“孩子,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帮上忙吗?”老先生温和问着,我擦干眼泪摇摇头。衣服使我渐渐温暖,“谢谢。”我哽咽着,他们没有忽略我的存在。
他们对望,老奶奶轻叹“孩子,你还年轻,这世上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,想开些吧,有什么事就和父母朋友说,别一个人闷在心里。”我忍不住扑到奶奶的怀中大哭,她只是温柔的抱着我,拍着我的后背,老先生递过手帕。这个怀抱我等了十几年,却不是父母给的。那句谎话“我没有父母”怎么也说不出来了。正因为我深爱着我的父母,才恨他们。
在他们家喝了热热的咖啡吃了一些糕点,我只是说和父母赌气跑了出来,隐瞒了真实的情况。他们劝我回家,“世上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父母。”这是老先生说的,也许吧,只是我父母的爱给了弟弟。
告别的时候他们将我送出很远,等我回头望--他们相携而行,平淡而幸福,朝阳刚刚升起,他们就迎着太阳而去,突然好羡慕、好感动。鼻子有些发酸,我揉了揉眼睛,向着他们的背影,微笑。
回到城市,仿佛美好的只是一个梦境,现实冷酷无情。在我旅行的这段日子里没有上网,原本以为网络已融入我的生命,如今才发现,只有在城市这个灰暗冷漠的地方,我才需要网络。我又龟缩到自己的壳里,这趟出游耗费了近两个月,我的体力透支得厉害,需要休息了。
屋里一层灰尘,门缝里塞了几张收费单和广告。恐怕除了水电厂煤气站没人记得我了。
(6)
网上的人陌生了很多,所有社区并没有谁因为我的消失而询问。Q上的朋友也只是互相招呼“好就不见了,还好吗?”“一般,你呢?”“也行:)”……这些谎言,我暗暗咒骂,我快死了,一点都不好,却仍说这谎言。谁会去真正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,谁又在乎谁,说了又如何,最多得到的是不痛不痒的“安慰之词”,可能会被人当成故事:我的一个网友快死了,是脑瘤。也可能转身之间就忘记了,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,永远体会不了那种切肤之痛。
“小姑娘,你哪里去了?”
“玩”
“去哪里?一个多月没见你了,想你”
“才怪”不用看昵称便知道是他了。
“真的真的,你这么久没来,我才发现我喜欢你。”
“算了吧,你,我还不知道”
“不算不算。你知道我什么啊?”
“你才不可能真心喜欢上谁(除非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),你最多是一时投入,过了便厌倦,遗忘了。”
“还是你了解我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?”
“不知道,但我知道你不是我心中喜欢的。”
“真无情,我真的爱你啊。”
“我信么?”
“……不信,你见我就信了。”
“算了吧。”
“又算。”
……纠缠不清,每次聊天都是这样,有些厌烦,却总觉得和他聊天是快乐的。他不太一样,没有问过我关于我现实的任何事情。
和他聊天仿佛渐渐变得必不可少。我知道他这种人要的我给我起,也知道爱上他是危险的事情。如果说我们都是毒药,那么我是烈性,发作快,立竿见影;而他却是慢慢的腐蚀你的骨肉,不自觉中让你中毒甚深,无药可救。
“见面吧!见面吧!见面吧!!!”一上来的开场白吓了我一跳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你的特殊,放过你或者当朋友太可惜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你不觉得虽然你我各走极端,但骨子里却是一种人吗?”
“哪种?”
“一直寂寞着,却渴望有人理解,哪怕是下地狱也有人陪伴身旁。”
“……”
“见面吧,我是认真的。”
“可我不是认真的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不为什么”
“给我一个理由!”
“需要理由么?”
“你瞧不起我?还是自己丑怕见我?”
“都不是。”
“那是什么?”
“不要逼我。”
“你还是看不起我?!”
“你认为身份背景重要么?没有谁瞧不起谁,只有自己瞧不起自己。不见你,如果你是认真的我不想伤害你;如果你不是认真的我不想伤害自己。”
“为什么这么说?我不会害你,我也不怕你伤害。”
“走了,再见”
“别走!说清楚”
“下次下次,你让我考虑!”
“就是见个面,怕我吃了你啊?”
“下次再说,8888”我逃也似的关上了电脑,把自己抛入床上考虑这个问题。
见了面我们会发生什么,我有这个预感,却不敢仔细想,不想连累他,却隐隐觉得该有一场恋爱了,如果就这样死去,我不甘心。也许该去医院确诊到底还有多少时间了。
(7)
至多一年。当拿到这个结果时,我无声笑了,这便足够了。让我自私些吧,不管别人,就挥霍着最后时光,更何况……也许他不会为我伤心,这样我便没有什么牵挂了。
(8)
当我坐在“上古”酒吧里,还有点不可思议,这便是约定的时间地点,就差那个人了,将是第一次,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搅动着“毒之泪”我的衣着安静与这里格格不入——白衣黑裙,刺目而无力。在角落里,冷冷看着那些快乐的孩子们,也许比我大,充斥着年轻人特有的狂傲浮躁。
有人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,我抬头——是目光深邃衣冠楚楚二十八九的男士,显然不是我在等的人。“我可以坐下吗?”“你已经坐下了。”“注意你很久了,这不是你这种女孩应该来的地方。”“也不是你该来的。”他微笑,“那一起出去走走吧?”我垂头不再说话,注视着杯里奇怪的惨兰的液体,没有勇气去尝试味道,仅仅是因为它的名字。
对面一阵骚动,紧接着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:“老兄,这不是你的位子。”人被拖离椅子的声音。他来了。看表,迟到了3分钟。乱乱的头发不羁的眼神充斥着不屑,偏又含情脉脉——他有一对桃花眼。第一个人想表达一下他的愤慨,在看到他撕破的衣衫上面点点血迹,左臂上一道不浅的刀口流出的血时,就乖乖溜走了。
“坐”我指指翻倒的椅子。他一言不发坐在我身旁,脚架在了桌子上手搭上我的肩膀。“那边。”
“这边不是更好吗?”他坏坏的笑,凑近我,热气喷在我的脸上,“像不像美女与野兽?”他回头向后喊,“兄弟们?!”口哨声响起,一片怪叫。“嘿嘿,不会吓倒你吧?我刚打完架,就和兄弟们一起来了。”
我没有回头,直望着他“和我有关么?你一身汗臭,建议你下次约人宁愿迟到也要去洗澡。”
轮到他呆住了,皱这眉嗅了嗅自己“有吗?……是有点……”
“坐到那边去,如果你还想见到我。”
这回很听话,他起身坐过去,他的弟兄们一阵口哨,他恶狠狠骂了一句。我喝了一口“毒之吻”,很辣,放下不再动它。
“你不害怕?你这种淑女怎么会不害怕呢?!”他皱眉,脚又搭在桌子上,我盯着看没回答。这次他自觉把脚放下去。
我掏了半天扯出一条手绢仍给他“我不想一会儿和死人说话。”
他笑了,痞痞的,晃动左臂“没事,小意思。”却还是拿手帕包扎了一下,后面又是怪笑。他伸手拿过桌上的牌号扔了过去,将他们轰走,顿时安静了不少。
“你有什么可吓人的?”
“黑社会啊。”
“我早说了不怕。”
“在网上还当你是随口说说呢,原来也有人这样说,见了面还是怕的要死。”
我冷笑。
“喂,美女,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”
“孟梦。”
“啥?梦梦?”
“姓孟,名梦。”
“好听好听,人如其名。”
我凝视着那杯鸡尾酒。
“别不说话啊,干坐着怪无趣的。对我印象怎么样?”
“还不错。”
“我帅吗?”
“算是。”
“我身体棒吧?”
望了眼他胳臂上的肌肉,“还不错。”
“对我满意吗?”
“嗯。”
他又凑过来小声说“那还等什么?咱们上床吧?!”说罢他仰到椅子上放声大笑。
我平静的看着他“好。”笑声猝然中断,他张着嘴看我。“闭上嘴巴。很不好看。”他猛然合上嘴。“害怕了?”他摇头。“对我满意吗?”
“满意。”
“那为什么反应这么大?”
“我、我没有想到,你这么淑女竟然这么回答。”
“我不是淑女,从来没有承认过。”
“可是可是……”
“这身衣服是我所喜欢的,不要以为长裙长发就是淑女。”
“哦……”他的眼珠再转,好像对刚才丢面子很不甘心。“那你还是不是处女?”
“重要吗?”
“当然,如果是,万一以后你缠上我怎么办?”
“不会。”
“你不是?”
“是。”
“我的魅力可是无人能抵挡的,不信你整天和我接触还舍得离开我。”
“一年,最多和你在一起一年。”
“不会吧?”
“长?那半年好了。”
“真不给面子,我一定要你爱上我。”
“你那么自信?”
“当然!”
“赌?”
“赌!”
“你输了找个贴着‘治性病’的电线杆子大喊三声‘我的病有救了!’”
“你狠!你输了……嗯~”他开始坏笑,“以后当我情妇,直到我厌倦了。”
“成交。”
“喂。”
“什么?”
“你还没有问我的名字。”
“对哦,你叫什么?”
他翻白眼,“杨尘。”
“可惜了。”
“啥?”
“名字,诗意在你身上看不出来。”
他嗤之以鼻,“那玩艺能当饭吃能赚钱吗?”
“……”
他端过“毒之泪”一饮而尽,“这是什么?”
“酒。”
“我知道。什么酒?”
“鸡尾酒。”他大翻白眼,我忍不住笑了。“回答没有错误啊。”
“什么鸡尾酒?不要告诉我是外国鸡尾酒。”
“毒之泪。”
“好,以后喝这个,味道还不错,就是淡了点。”
“走吧。”
“再见。”
“喂,是你和我一起走!”
“去哪?”
他抓住我的手,“make love~。”听到的人开始窃笑。
我甩开他。“停——”
“怎么?你答应的,不能反悔!”
“不是反悔,第一,你我才是第一次见面,我不想这么快。第二,我不希望你的血弄到我身上,”我指指他的左臂,血又渗出了,“第三~你一身汗臭,离我远些!”
“这么多规矩啊,真是麻烦。”他嘀咕。
我拍拍他的肩,“你再等等吧,兄弟。不行就先去找那些ppmm。走了,再见。”我走出门口。
“喂,就这么走啊?我送你!”
我没有回头,摆了摆手,融入夜色中。
(9)
相见分离,多半都是在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隐藏在黑暗之中,随便一家酒吧喝着酒,相对无言或是听他讲打架的经历。他很少问我的过去,我也没有过去,正如没有未来一样,只是这么活着。
至今为他裹伤口用去我九条手帕了,他打架的频率不高,一、二周一次而已,但每次都会带伤,我没有劝阻过。与他相处自然而无优,不用担心什么,生命是自己负责的,无人能左右。有两三次喝着酒我便突然晕过去,每次醒来身上都有他的衣衫,而他坐在对面,抽着烟,深深望住我,眼神中的怜惜疑惑与不安没有掩饰,我从来不说原因,他也不问,仅仅是突然抱住我,很紧,我透不过来气。他可能猜到了什么,却无法肯定。
在他狂放不羁的面具下面是沉默而悲哀的心。他打架、无所事事、上网见面,仅仅是为了不被那空虚的寂寞抓住,他逃离不去思考,因为脆弱而冷漠。当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,他总是疲倦的枕着我的腿,如同孩子一般,仰望着城市之中仅有的几颗星,看着看着,就这么睡去。河东公园里的长椅便成了我们夜晚的住处。
梦梦的自述(10)
农历七月十四,鬼门开。寂静的夜晚,在这繁华的楼群中一些人默默烧着纸钱,灰四下飘散,一种令人窒息恐惧的气味便弥漫开来。
“你相信鬼么?”
“不知道,在我没有看到之前不会肯定它的存在。”
“据说,白天人看不见鬼,晚上鬼看不见人。”
“……”他楼紧我,“我想喝酒。”
“去哪里?”
“我家有个吧台。”
“走吧。”
第一次走进他租的小屋,不大,只有一间客厅加上9立方米多的卧室。很空旷,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立柜。客厅里则是一台电脑,几个软垫,外加小小的吧台,竟有不少酒。
“你不看电视么?”
“无聊。”
我耸肩。
他敏捷地跳过去敲着酒杯“小姐,请问要点什么?”
“毒之泪。你会配么?”
他吐舌头,“我只会把各种酒掺在一起。”
“那还是给我杯香槟。”
他递过来,挨着我坐下。于是我们就在一盏昏暗的壁灯下默默喝着酒,看着窗外——尽管漆黑一片。
“我想……我这样的人只能下地狱。”他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内乱撞,我握住他的手,“那么我也去。”他轻轻的吻我,“可以吗?”我抱紧了他,杯子掉在了地上……
好寂寞阿……即使相拥在一起,也无法温暖心底的凉意,在欢狂的最深处却有想哭的冲动,不为了什么,仅仅是两个人更加寂寞了。汗在晚风中逐渐干了,他的床好舒服、他的气味好安全、他的怀抱好温暖,我沉沉睡去。
醒来时天已大亮,他不在身旁。感觉疲乏得不想动,翻了个身便又滑入梦乡。朦胧中有人在捏我的鼻子,很不情愿的睁眼,他笑眯眯的坐在床边,“很累吧?”我的脸顿时红了,“嘿嘿,吃点东西补补。”他端过一个托盘,上面放着很多吃的。
“你做的?”
“是啊,尝尝,你有口福了,我还是头一次做饭给不是我妈的女人。”
我微笑,“真的啊?好孩子。”
“你占我便宜啊?快趁热吃吧。”
“我穿衣服,你先出去一下。”
“喂,还害羞啊?我就在这里看着你换。”
“去去去去!”我拿枕头丢他,他笑嘻嘻的跑走了。
(11)
之后,我就和他住在一起。他不在的时候我便写下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,我的记忆好像在逐渐衰退,精神无法集中,思维飘忽不定,常常几天几天头痛的睡不着觉。我知道,时间不多了,要抓紧做一些事情。我不想死在他的面前,不想看到他的眼泪,我真的,爱上他了,虽然我从未对他说过。
他察觉到什么,总是要带我去医院,不再让我喝酒熬夜,越来越温柔,虽然他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,但我明白他的心意。
冬天里的第一场雪就这么落下了,很大,满天鹅毛飞舞,在这孤独的城市中很少能够看到这景色了,那天农历腊月初七,我的生日。他不知道。我已经23岁了,不能算夭折。春节他想带我去见他父母,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活到那个时候。
(12)
那天我醒得很早,五点多,外面漆黑一片,他还在熟睡,我轻轻吻他如同纯真大孩子的脸庞,泪滑落在他的脸上。
带着提前收拾好的行李,我独自上路。
不知道何去何从,却清楚不会留在这里,不会再回来。天很冷很阴,没有风,我就这么离开生活了近十年的城市,义无反顾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