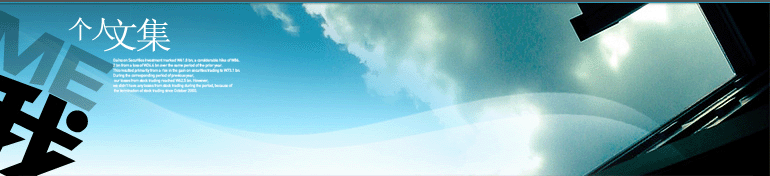|
没有所谓尖锐、疼痛的青春,有的只是一败涂地。
(1)
“云宁,你真的很白痴,”远夏摇晃着头说,“这道三角函数题我至少跟你讲过一百遍了,你竟然还不会!”
“是的,我就是白痴。”我毫不否认。“你是大天才又怎么样?谁叫你是我哥哥的?你就得管我!”
远夏小声嘟囔:“偏不管你,小丫头片子。”
我听见了,马上大声还击:“你敢?!老男人片子!”
这时姑姑的声音就会从隔壁传来:“远夏,这么大了还不懂事,跟妹妹争什么呢?”
“没什么,闹着玩呢!”远夏心虚地回答,然后把练习本推到我面前,恶狠狠地道:“白痴,重做!”
(2)
“你怎么说普通话?”在这个南方城市,几乎每个初次和我碰面的人都会这么问我。
“因为我在北方呆过几年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
“那你会说本地话吗?”
“不会。”
“唉呀!”她们无一例外会叹息一声,拿一样的眼光瞅我,好象我身上缺胳膊少腿似的。
只有一个叫明熙的男孩,过来对我说:“云宁,你可不可以教我说普通话?”明熙有着很大很明亮的眼睛,睫毛浓密得让女孩们妒忌。
我只对他说了三个字:“别烦我。”天生对这种看上去乖巧、讨老师喜欢的学生反感。
明熙远远走开,脸上没有表情。
但是班主任偏偏安排我与他同桌。
(3)
给远夏写信:“哥哥哥哥哥哥哥哥``````”写了满满三页纸,然后撕碎,扔进垃圾篓里。
我找不到更多的词语可以写。
这里,不会有人叫我“白痴”。
(4)
我试着融入这个城市。
地理书上说,这里的气候很好。没有北方冬春肆虐的沙尘暴,没有深及膝盖的大雪。空气湿润而暧昧, 像一壶温吞吞的永远烧不开的水。
这是我曾经生活过九年的家乡。曾经而已。对这里的人来说我是个异乡人。在北方的时候别人也认为如此。
我一直是没有家的人。
(5)
与全班男生为敌。
已经习以为常。从小学到初中,都是这样子。
放学时开始吵。七个男生对我一个。
他们都才十三、四岁的年纪,骂出来的话丝毫不比成人逊色,句句都设计到人的生殖器。
我只不停的重复:“卑鄙无耻下流肮脏龌龊``````”似乎在作无用功。
他们开始推我、搡我,几个人堵住我不让我躲闪。
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“我看不起你们!你们不配和我说话!”
我的眼镜被踩成粉碎,书包从四楼扔了下去。
他们一哄而散。
我趴在座位上低声叫:“哥哥,哥哥,哥哥`````”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掉。我变得懦弱了,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哭的。
暮色四合,想起校门将闭。抬头,看见书包搁在讲台上,乖乖巧巧的样子。
窗外有人影闪过。心中一动。
但那不会是远夏,不会是我哥哥。
(6)
喜欢金庸、古龙、黄易;喜欢“仙剑”、“星际”、“拳皇”;喜欢《青春》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``````我喜欢着这些和我外表看上去极不相符的东西。
因为它们都是远夏喜欢的。
十三岁那年,远夏问我:“云宁,想不想跟我学吉他?”
“当然想!”我答。事实上,这句话我已梦寐以求了四年。
“学吉他很苦哦,要把手指头磨出茧来。”他伸出手掌,给我看那上面厚厚的茧。
“我不怕,”我说,“你一定要教我,不许反悔。”
远夏没有反悔,我也没有学会吉他。
那个噩梦般的夏天,我不得不离开北方,离开远夏。
妈妈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花三年时间缠着她给我买吉他,因为我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。
高中的时候,吉他终于买来了,却从来不弹。
它立在电视机旁,应该不会寂寞。
(7)
开始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孩子。
头发理成板寸,穿很宽大的滑板服,管几个女生叫老婆。
“云宁,你是不是变态?”
“呵呵,我是同性恋。”我很认真的告诉他。
于是我在校园内开始大大的有名。
不少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我把头扬得更高。
有男生试探地邀我去打电游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出来时我坚持付钱。
当初那几个围攻我的男生也频繁地来邀我。每次都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当然,结帐的时候一样很爽快。
我只玩“拳皇”。不停地找人单挑,不停地输。到后来几乎没人愿意和我对打了。
除了一个叫何宵的男子。
之所以叫他“男子”,是因为不知该称他“男孩”还是“男人”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在电游室碰见他。
他留着很长的碎发,刘海垂下来遮出眼睛。左耳戴着一只银质耳环。皮肤很白,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样子。从他的外表我猜不出他的年龄。
男生们指点我去找他。因为他是这一带玩“拳皇”最厉害的人。
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摆在他面前:“喂,你教我玩。”
他连头都未抬,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:“小女娃,不要这么‘猛’。”
“我想让你教我,”我生硬地说,“拳皇。”
他把钞票丢给我:“女娃子不适合玩这个。过家家去吧。”
“我不是女娃子!”
他终于抬起头,乜斜着眼,脸露讥嘲的笑容:“那你是什么?”
“你管不着!”
“听说你是个同性恋?”他脸上的笑容更深。
我愤怒地瞪着他,一言不发。
然后他俯身凑在我耳边轻声说:“告诉你,我也是。”
(8)
转学半年后在亲戚家里听到了远夏结婚的消息。据说婚礼办得很豪华,很热闹。
那天我在电游呆了一整晚,疯狂地玩“拳皇”,手掌被操纵杆磨出血。
何宵给我手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卫生纸,边缠边说:“你忍着点。这么晚了没地方给你买创可贴去。”完了他问我:“你今天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?”
我避开他的眼睛:“怎么可能?考试没考好,不想回家听老妈唠叨。”
“是吗?”他脸上又露出讥嘲的笑容:“我没想到你还在乎成绩。”
“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!”我不客气地顶了一句。他扭过头继续在街机上“奋战”,不再理我。
偌大的电游室里只剩下我跟何宵两个人。老板在吧台后面昏昏欲睡。
忽然感到浑身发冷。
“何宵!”我叫着他的名字。
“有话快说,有屁快放!”他硬邦邦地道。
“你做我哥哥吧。”
他背对着我。空气里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街机发出古怪的声响。
“你聋了吗?”我一锤子砸到他肩膀上。“你说话呀!”
“你害我GAME OVER了。”何宵转过身来,似笑非笑:“我正在考虑该叫你‘妹妹’还是‘弟弟’呢。”
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
(9)
十三岁之前我只有一个哥哥,他叫远夏。他现在与我毫无关系。
十四岁之后我有了一个哥哥了,他叫何宵。至少目前他与我关系很“铁”。
但是,以后呢?
(10)
回到学校,已经过了早自习的时间。
明熙小心翼翼地问我:“昨天晚上你上哪儿了?”
我厌恶地横了他一眼:“不干你事!”
“班主任早上在班里挨个盘问呢。”明熙小声说。“我跟老师讲你回亲戚家了。呆会儿老师问起你,你就这样讲,啊?”
“谢你好意,”我说,“以后请不要多事!”
“聂云宁,”班主任走进教室,像猫逮到耗子那样盯着我,“你妈妈大电话告诉我说你昨天一夜没回家。你干什么去了?”
“没什么,老师!”我站得笔直,很大声地回答道:“我打游戏机去了。”
我看见明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(11)
不管在哪里,我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。
班主任把明熙和我调开,理由是“明熙原本是个很诚实的孩子,跟你坐在一起后就学会谎。”真是可笑,一学期里我跟他说话总共不超过十句。但是“罪名成立”,我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。
母亲对我说:“你为什么要回来?你呆在你姑姑家不好吗?你自己不检点也就罢了,不要让我跟着丢脸!”
是的,我问自己:我为什么要回来?为什么要回来?
(12)
“啪!”远夏的手掌响亮地扇在我脸上。
“云宁,你回去吧!这儿容不下你。”远夏的脸上写满失望。“你简直是无药可救!”
我最爱的哥哥打了我。他根本就不愿听我一声辩解。我站在那里,浑身颤抖,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门冲我重重关上。
可是哥哥,我真的没有撒谎。
可是哥哥,我真的没有撒谎。
可是哥哥,我真的没有撒谎``````
(13)
走进教师,看见桌子上躺着一张卡片:
明天是我15岁生日,来我家参加我的生日PARTY好吗?
明熙
抬头四顾,发现班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这种卡片。
我把卡片攥在手里三秒钟,然后机械地撕成碎末,冲进下水道里。
两天后在走廊里碰到明熙。
“云宁,你昨天怎么没来?——你收到我的请柬了吗?”他开口问道。
“没有——我不知道什么请柬。”我回答,头也不回地走进教室。
忽然觉得自己真他妈的贱。
(14)
远夏已经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我对此不感到惊讶。如果说有,也只是惊讶于自己的平静。
“哥哥,恭喜你了。”我在电话里说。
“是云宁啊,”远夏的声音依然悠扬悦耳。“好久不见,怎么一直都不打电话过来啊。是不是把哥哥忘了?”
“怎么会呢,哥?”我答:“小外甥可爱吧?”
“是啊,很可爱!你呢?你过得好吗?”
“很好。恩``````我嫂子怎么样?”
“她也很好。”
``````
“没什么事就挂了吧,”他说,“别浪费电话费。”
“哦,好。再见,哥哥。”
“再见。”
听筒里传来“啪嗒”一声,接着是断断续续的“嘟嘟”声。
我握着听筒,想哭又想笑,
我们都表现得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?
(15)
明熙转走了。这件事在班上并未引起半点波澜。他本来就是那样平淡无奇的一个人。
只有班主任不无遗憾地说了句:“该走的不走。”她的眼光停在我身上。
我装做没有听见,若无其事地低头看小说。
只是有一天,当我无意间回头望见那张挪到我后面的空荡荡的桌子时,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难过。
那个睫毛很长,眼睛很亮的男孩子,我还欠他一句:“对不起!”
(16)
“云宁,你就要初中毕业了吧?——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了。”何宵对我说。
我盯着屏幕:“你也在乎这个吗?”
“恩。”他用少有的肯定语气回答:“我最近也不会来——马上就要高考了。”
我转过身,疑惑地望着他。
“奇怪吗?”他自嘲道,“我已经是两届的‘高四生’了。”
(17)
我上了一所二流高中。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何宵。听别人说他去了北方的一所大学。
这是我才发现除了知道他叫何宵外,其余的一无所知。
我叫了他整整一年“哥哥”。
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家电游室。
(18)
班上竟然还有一个说普通话的人,并且比我说得还标准。他叫沈言,是地道的北方人。
“世上哪有那么多同性恋的人?”人群中,沈言的声音尖锐地刺入我的耳朵。
我提着一袋面包,笑容满面地对一个女生说:“亲爱的,我给你带早饭来了。”
(19)
班级联欢晚会上,沈言带了一把吉他来。
他唱:“我只能一再地,请你相信我,那曾经爱过你的人,那就是我``````”
——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
我猝不及防地泪流满面。
(20)
“我只能一再地,请你相信我,那曾经爱过你的人,那就是我``````”远夏的声音有如天籁。
这首歌,我如痴如醉地听了四年。
最后一年,是站在远夏的房间外面,听他弹给他的女朋友听。
我曾在远夏门外怎样的流泪,远夏永远不会知道。
我知识他不听话的、逐渐变坏的妹妹。
我的改变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我走进教师的时候,全班每个人都注意到我脑后扎起一条单薄得可笑的辫子。
沈言在路上拦住我,眼里盛着浓浓的笑意。
“你准备做个正常人了吗?”他问。
“我从来就没有不正常!”我反驳。
“是吗?”他勾起嘴角,“——我还以为你是为我改变呢!”
“你可真是会做梦。”我讥诮道。
“那天我看见你哭了,”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,“你不必对我隐瞒什么。”
(12)
想起已经很久没玩过“拳皇”。
无意识地逛到一家电游室前。正是生意最好的时段,不时有人进进出出,嘈杂的声音隔了很远也能听见。
一帮男孩子从里面出来,边走边谈论刚才的战绩:“手真臭,以后再不玩拳皇了。”
我笑笑,想当初从何宵那里学来的一手绝技是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了。
那个叫“何宵”的男子,再不会出现在这里。
然后左手腕莫名地痛。
“你手腕上那条疤是怎么来的?”何宵有一次问我。
“小时侯爬树刮伤的。”我答。
这理由很合理,何宵丝毫没有怀疑,连我自己都快信以为真。
那个十二、三岁的孩子对着浅浅的血痕无声痛哭——当她拿起刀片割向手腕时,竟然搞不清血管在哪里。
远夏说得很对,我真的是个白痴。
(23)
“你可不可以做我哥哥?”我对沈言问了一个很快让我后悔不迭的问题。
“我不需要妹妹!”他断然否决。“对我来说,异性只分两种:女朋友和陌生人。没有第三种可能。”
“我``````不可能会喜欢上你的。”
“你考虑清楚,”他说,“你对我感兴趣——我看得出来。”
“不是你想的那样``````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(24)
终于还是决定去找沈言,但是到处都看不到他人影。
“他在小树林那边练琴。”有人告诉我,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我没有在意。我只有一个念头:赶快找到沈言。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。我怕我下一秒钟就没有勇气说出口。
迎接我的,是一对纠缠在一起的躯体:沈言正和一个女生忘情地拥吻。
我的大脑刹那间一片空白。“逃呀!”一个声音对我说。我用比来时快一百倍的速度逃离此地,不停的跑,直到双腿失去知觉。
眼前又出现世间最丑恶的一幕:两具赤裸的身体纠缠在一起翻滚——是姑父和一个陌生女人。
那个夏天,姑姑出外度假。
恶心,极度的恶心,我开始呕吐,想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。
“哥哥,姑父他``````他是个坏人!”
“他骂你了还是打你了?”远夏说,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“哥哥``````姑父他嫖娼。”
“云宁,你胡说些什么?”远夏满脸厌恶,“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招人喜欢?”
“哥哥``````”
“我警告你,云宁,你再这样无中生有就别想呆在这里!”
好的,哥哥,只要你肯让我留在你身边,只要你能分给我无论多微小的爱,我可以什么都不说,什么都忍受,哪怕深厚总有一双肮脏的、窥视我的眼睛,哪怕我整整一个夏天,洗澡都不敢脱衣服。
(25)
再见到沈言,我表现得若无其事。
这个讲普通话、会唱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的男生,他不可能会成为我哥哥。他只是个陌生人。
想起他的那句“名言”,觉得由我来用也很合适:对我来说,异性只分两种:哥哥和陌生人。没有第三种可能。
(26)
高中过去一半。无悲无喜的生活。
远远地,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,斜倚着栏杆。
“哥哥!”我大叫,朝他直奔过去。他望着我,笑容如清澈蓝天。
“哥哥,真的是你!”我抓住他的手,确定眼前这个人真真切切的存在。
“我还能有人仿冒么?”叫何宵的男子说。
我们找了一间小酒吧。
“你怎么会突然来看我?你不是在北方吗?”
“我早就回来了。事实上,我在那边只呆了两三个月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我不适合北方。”他笑起来,“当然,最主要的是——想你了!”
“哥!”我有些恼火,“不要拿我开玩笑!我要你说实话。”
他苦笑了一下。“说什么呢?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北方。云宁,我去那里,只是想知道那儿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牵肠挂肚。可终究还是被那边的沙尘暴赶了回来——很没用,是不是?”
“哥哥``````”鼻子发酸,可是流不出眼泪。
“后来我就去了南边,那个如暴发户般崛起的城市。其实我想去的地方一直是那里的一所美院,可是花了三年时间都没有进去——我总以为我不会被第一志愿录取,但偏偏``````”他停了下来,伸手倒酒。
“云宁,你恋着北方;而我,只能属于南方。”何宵的声音,疲惫而悲哀。
(27)
桌子上躺着一封信,字迹陌生。
“``````你一定不记得我是谁。初中时那个有幸与你同桌半年的男生,此刻怀着深深的愧疚之心写信给你``````”
“``````看到你被人欺负而无法施以援手,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``````”
“``````尤其不能让我原谅自己的是,由于我的疏忽,全班就只有你没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。那件事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吧``````”
“我的18岁生日就要到了,这次你能来吗?”
看到署名:明熙。
那个单纯如斯的男孩子,我连他的面孔都已记不清。
信封上没有留地址。
很想为自己的初中大哭一场。
(28)
“云宁,你变了这么多。”何宵指着我长以及肩的头发,温和地笑,“是为某个男孩留的吗?”
“永远不会有那个男孩的。”我答。
“不要说得这么绝对,云宁。”他眯起眼睛。“你根本就不是同性恋``````”
“你``````”我又惊又怒,像刺猬突然被拔光了所有的刺。
“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,我就知道。”
“是吗?”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“是的,”他继续说道,“当然,我也不是你的‘同类’。当初之所以那么说,是因为不想当你花钱买来教你玩游戏的‘工具’。”他顿了顿,“可也没想到会当了你的哥哥。”
他直视着我的眼睛:“云宁,你想听真话吗?其实我——”
“不,哥哥,请你不要说,”我惊惶失措地打断他,“我知道,你一说出来,我就没办法喜欢你了,一切就都完了。真的,哥哥,求你不要说好吗?”
他一动不动,眼里的光亮一点一点地退色。最后他轻轻地答道:“好的,云宁,我答应你,我不说。”
(29)
左手腕又在隐隐地痛。
远夏的歌声那么遥远。
他订婚了,幸福的那个女子是我的小学老师。我站在远处观望,用力咬住自己的手腕——那道伤口还没有愈合。
他们相识于一次家长会。远夏找她询问我为什么老是被班上的男生打得伤痕累累。
如果,我一直是个好孩子。
只是如果。
从此再没有一丝一毫属于我的幸福。
订婚典礼后,我明白,我成为这里最多余的人。
“远夏还没有教我吉他。”我对自己说。“他不可以反悔。”
但这条借口是多么不堪一击。
(30)
“哥哥,我们认识四年了吧?”我对何宵说。
“是啊。”
“那哥哥,你很快会厌烦我的。”
“猪头,怎么会呢!”何宵敲了敲我的额头。“你太爱胡思乱想了。”
哥哥,我们能永远这样子对不对?永远这样子``````
(31)
给远夏打电话。
“哥哥吗?我是云宁。”
“哦,云宁,是你啊。你过的怎么样啊?”
“还好。你呢?”
“也还好,就是忙得不可开交。”
“这样,代我向嫂子问个好。对了,小外甥会说话了吗?”
“云宁,你记性怎么差?”远夏在电话那头哈哈笑道:“他都三岁多了,上幼儿园呢!”
就在那一刹那,我清晰地感觉到,有什么东西飞快地掠过去了,一去不复返了。深藏在脑海里的隐秘之核突然被打开,在阳光下消失于无形。电话里传来的那个声音不是远夏,而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,身材开始变形,每天忙着上下班,接送儿子,给妻子做饭,不会再有时间玩“拳皇”,也不再会有心情弹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
真正的远夏已经永远消失在那个夏天。
“``````云宁,你现在高三了吧?学习怎么样?”电话那头的男人问。
“不是很好。”
“‘唉,要努力啊。争取考到北方来。可以随时到我这边玩,多方便。”
“恩,我尽量。”
“什么尽量嘛!一定要来!”
“恩,哥,我会的。”
我挂了电话,看了看天,整个世界突然如水般安静。
“哥哥,我喜欢你,喜欢了整整四年。”这句话我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也没有必要再说出口了。
(32)
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。
那个初到北方的孩子,总是记不住从学校到姑姑家的路。
她坐在远夏的自行车后架上,偷笑着听哥哥用无奈的口气训斥说:
“云宁,你这个白痴丫头!说过多少遍了,回去的方向是向南,拐弯,再向北``````”
|